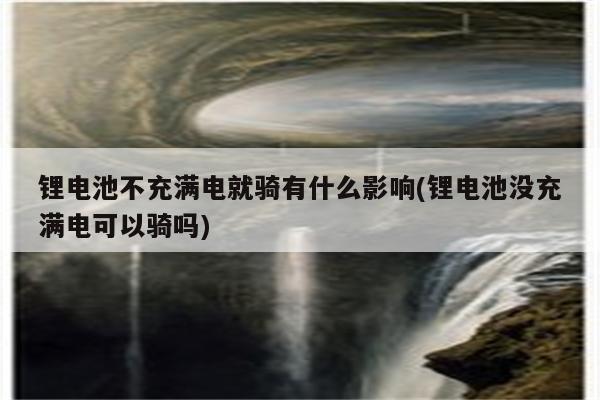我和我的父亲(全)
去年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早几年有了自己的小家,也时常牵挂着原来的大家。自从儿子上幼儿园以后,就想通了一些道理,所以不断的劝说自己对孩子不必太过严苛,也慢慢的收起了为他准备的戒尺,为了做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爸爸!
我的父亲叫李发明,也许当初爷爷给身为长子的父亲取名的时候,也是抱着非常多的期望,同时怀着一丝丝的忐忑给取了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父亲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发明,他在我上高中之前,都是一个农民;而后去厂子里上班,用当下的三个字概括一下就是:农民工。
父亲姐弟五个,我只有一个姑姑,我对于父亲最初的印象,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骑在他的脖子上,他拉着我的两只手,和妈妈一起从奶奶家回自己的家,两个姐姐在不在我已经不记得了,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还是很贫苦的。我们从奶奶家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沟坝,沟坝两边都是水塘,坝子有两米多宽,也是平时去圩上的唯一通道,坝上开了一条小水渠,在放水。我们经过水渠的时候,一条大白鲢静静躺在水渠的中间,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的刺眼,像家里那一把切纸大刀一样光亮!这条鱼当然用于改善一家人和爷爷奶奶第二天的伙食了。
为什么说像我家里那一把切纸大刀一样光亮呢?因为家里真的有那么一把锋利无比的切纸大刀。有经历的人,应该知道。农村里总有红白喜事,办事的时候,放鞭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虽然至今我也没弄清楚原因,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总是让那时的我感到激动又神秘!没错,我家就是业余做鞭炮的。90年代初这种小作坊还没有受到政府的管制,农民在种地之余还可以做点类似于这种小生意补贴一下家用,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做鞭炮的整个过程,因为我时常在边上观摩,偶尔还能帮点忙,两个姐姐就不一样,他们是真要干活。那把切纸的大刀是我认为至今我见过的,最锋利的一把大刀,因为它可以将一捆和足球差不多粗细的纸,在我父亲的手里一刀切两半,并且切面光滑平整。我认为我还是有必要向大家展示一下90年代皖西农村整个鞭炮的制作过程,因为那贯穿了我很大一部分的童年。
父亲在二十四五岁的年龄娶了妈妈,听我妈说媒人是我姑姥姥,也就是我外公的妹妹。当初我外婆是不愿意这门亲事的,无奈我姑姥姥和我奶奶交好,威胁我外公不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两家就不走了,没办法,我妈就嫁过来了,说实话,有时候我内心会忽闪一下的感谢我姑姥姥,毕竟没有她的坚持就没有我。
为什么扯这一段呢?因为我妈嫁过来,就把他们马头镇的瑰宝之一——鞭炮也带过来了。父亲是做事非常细致的人,父亲在做鞭炮上,可以说是一丝不苟,颇有现在传说的工匠精神。那时我妈结婚陪嫁过来的衣柜,里面装的大部分不是我们的衣服,而是从印刷厂里拉出来卖给我们的印废的书纸,切得整整齐齐,上面还印了很多我不认识的字。这些纸一般都是用蛇皮袋或者麻袋装一袋一袋地放在衣柜里,避免放在外面受潮,毕竟那时候住的还是冬暖夏凉的土房子,湿气重。这些纸就是制作鞭炮的原料之一。
一开始,爸妈会用电焊条把一张张纸卷成一个中间空心的纸筒,这个工作只有大人能做,因为小孩子没有那么大力气把纸卷得足够紧,然后用浆糊糊一下边,晾干,再把纸筒染上喜庆的红色,再晾干。然后就是父亲上场了,把一个个纸筒捆成足球那么大的一捆,一捆上要间隔扎上好几圈尼龙绳。再用家里的大刀把一捆纸切成一盘一盘高3厘米左右的纸筒,这个工作只有父亲能完成,因为他足够的细致,力气也足够的大。后面就是和黄泥浆,把切好的一盘一盘的纸筒一端用黄泥浆封底,这其实看着简单,实际上对经验和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因为泥浆的黏稠度,封底的泥浆多少对鞭炮的质量影响很大,泥浆不够稠和封底的泥浆太薄,会导致鞭炮爆炸时把底冲掉,鞭炮不够响,用农村的话说就像放屁一样;泥浆封底太厚会占用纸筒的空间导致后面填装的火药量少,鞭炮有很多不能爆炸,也就是落果,而这些在我爸手中都控制的游刃有余。封底完成后就是把一盘一盘封好的纸筒放在太阳下晾晒,让黄泥干结。这时候也是配药的时候,配药也就是配置鞭炮用的火药,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过程,因为火药不是成品买过来的,需要自己买回来原材料自己配制,所以需要把白磷,硝等一些原材料过细筛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时候家里是一点薪火都不能有,我们一般也只能远远的看着父亲一个人在堂屋中间做火药,做完后成品的火药放在哪里我们也一直不知道。后面就是在盘底干结后糊一层薄膜纸插孔装火药,避免火药装到缝隙的同时要把火药均匀地装到每一盘,然后由我们姐弟三个人负责插引信,那个时候觉得差引信应该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了吧!虽然我只是偶尔客串一下,两个姐姐都是正经地坐那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引信插好了就交给老爸封口,封口就是把一个类似于扁头起子中间磨个口子,后面用破布包起来包成一个成人拳头那么大,顶在肩上,把小的那头对着插好引信的一边用力一顶,纸筒就挤进去把上面的口封住了,同时引信还不会受损可以顺利的点燃里面的火药。妈妈在老爸完成这一步骤后,就会把一盘一盘挤好的鞭炮拆散,一个一个的像编辫子一样编起来,大的大炮在前面最先编进去,小的在后面。一挂鞭炮一般都会有固定的长度,有的一两米,也有好几米甚至别人定制得更长的鞭炮。编好的就整齐地盘起来,用报纸封好装进大纸箱里面等别人买走,一般重要的节日和过年的时候,我们家里西头的屋子就会被搬空。因为爸妈做的鞭炮质量好,响亮而快速,在过年的时候总给人新年更美好的憧憬……
父亲平时除了种田做鞭炮之外,在村里有人盖房子的时候还会去做瓦匠,他应该不是生下来就会这些,但在我眼里他却是一开始就会了。那时候我家住的是土房子,所以对于别人红砖墨瓦盖起来的房子很是羡慕,有时别人的房子上楼板或大梁,图个吉利都会从高处撒些花生糖果米糕之类的让大家去抢,他从斗里面把东家的花生糖果往下撒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看他儿子在哪里,朝我多扔了两把!
那个时候的父亲应该是他最自由快乐的时候,虽然贫穷,每个人的身上都打着相同大小的补丁,每个人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能看到的人们都过着一样的生活,孩子们也都是玩着泥巴……虽然村里有几户盖了楼房,但大家大部分都还住着土房子。况且那时候,父亲自己也还是有依靠的孩子,虽然分了家,爷爷奶奶就在身边,很多事也还是爷爷奶奶主持着大局。现在的我是很难想象三个孩子夫妻两个是怎么养活过来的,但我认为那个时候家里是开心快乐的,因为一家人都在一起。
后来,最小的我上小学的那一年,家里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爷爷骑摩托车晚上回家连人带车掉进了沟坝西边的塘里,那时候塘还是比较深的,只记得夜里父亲兄弟几个都去捞车子去了,第二天我看到了带着塘泥的车子和显得枯瘦的爷爷,再后来,家里人就知道爷爷得了癌症,胃癌,他自己很早就知道了,瞒了家里人很久,拖到了晚期。几个兄弟在农村的那点收入,除了果腹和孩子上学之外,对爷爷的癌症已经做不了什么,爸妈了解到我姑姥姥家女婿也就是我三姨父在外面种蔬菜,还过得去,所以我爸借了几千块钱,带着我妈和我投奔我姨夫去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农村,看到那么大的世界——上海。
去上海,印象中我们一家人三口人乘坐的是农村的那种拖拉机到了镇上,带了不少叮叮当当的东西,再从镇上乘坐那种中巴车去上海,我对身边的事物感觉到无比的新鲜,包括中巴车,不停的问这问那,后来司机大叔索性让我坐在驾驶位边上的发动机盖上面,上面垫着厚厚的破布垫子,那时候已经深冬了,天气冷了,坐在发动机盖上很温暖也就慢慢睡着。在朦胧中经历了嘈杂,然后三轮车哒哒哒的马达声,父亲扛着喘气的声音,再后来就安静了,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被哐当哐当的声音吵醒,在去上海之前已经知道姨父他们住在火车道边上,一骨碌爬起来去看火车,然后就数啊数,不知道数了多久。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记住的是那时候爸妈的表情,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惶恐,无助,充满担忧的吧!
他们最先想办法把我上学的问题解决了,每天跟着表哥去上学,学校是老家的人在上海办的学校,叫长安小学。他们早出晚归的我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有天早上起来发现姨父家的大盆小盆里面养的全都是鱼,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迫于生计,老爸拿出了他以往在老家的看家本领,晚上和我姨父出去打鱼去了。
说是老爸的看家本领,应该算是他的爱好,农村的沟渠野塘很多,他没事就扛着挑网和鱼篓出门打点小鱼小虾回来改善伙食,听他说只要有人那么大的空隙,他都能把挑网放下去打到鱼,这也是我后来在我外公家学到的本领之一。他把渔网带到了上海,和姨夫一起,夜行某个倒霉的上海人的鱼塘,化缘了一些鱼回来,这也是上海人不喜欢安徽人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他们太穷了。
大概过了一周多的样子,我们搬到了新家,更加艰苦的生活开始了。姨父帮我们把东西送过去的时候,好像东西都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那是一块方方正正的农田,农田的南边是一条长满革命草的小河,新家在农田的北边,房子是用毛竹做框架,用稻草和泡沫皮子搭起来的,我知道这个房子一定就是爸妈早出晚归的作品,并且这更多的是父亲的作品,因为就算是一间茅草屋,都搭的那么精致,比周边其他人的茅草屋都好看很多,每个竹蔑的宽度都差不多,并且都在同样的高度和间距穿铁丝捆外面的稻草,每个铁丝头都朝外扭的恰到好处再折回去扣到草里,里面每块泡沫皮子的压缝都处理的恰到好处。但是房子里面就真的是家徒四壁了,没有桌子,没有床,没有板凳……什么都没有……爸妈去外面找了很多稻草铺在地上,我们就睡在地上,放学我就趴在稻草上写作业。
上海的冬天貌似比安徽还要阴冷,那一块租来种菜的田,原来是用来种水稻的,从那土的细腻来看,爸妈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在翻地上,撒了化肥种子,就是不见冒芽。干等着不是办法,家里快要揭不开锅了,我妈急的就拿个蛇皮袋子出去挖荠菜,挖马兰头,5毛钱一斤,一天跑几十里,挖回来摘干净也就换不到10块钱,有时候周末我会跟我妈一起跑,多少能挖点,所以荠菜和马兰头的样子是刻在脑子里的,无论现在的荠菜长得多奇怪,我都能清楚的分辨出来。父亲去卖荠菜来回的路上会去工地捡一些破的木板,回来用尺子量,锯子锯,钉子钉;慢慢的家里有了小凳子,小桌子,床,灶台这些东西,我也不用再趴在地上写字了。
记得一次是周六我妈挖荠菜中午没回家,家里第一次改善伙食买了一次猪肉,估计老爸也是觉得我很馋了,没摸过锅铲的他决定中午把肉红烧了,我当时也是满心欢喜又略带一丝担忧,怕他把这来之不易的一顿肉给毁了,所以全程在旁边指导,从小经常因为扒锅台没少挨我妈钉钉掴子揍,耳濡目染的肯定比我老爸强多了!所以中午那顿肉除了黑了点,其他的都还凑合,那也是我印象中老爸唯一一次摸锅铲,以后再也没见到了。
现在身边的很多人经常说我爸妈看着不像年龄差不多,感觉我爸看起来更老一些,头发现在也掉了不少。我知道,因为那是熬夜熬出来的。在上海种菜的日子一过就是十来年,我也见证着父母从三十出头迈入奔五的年龄。种蔬菜每天白天都在地里忙,把成熟的菜采摘干净,洗好在框子里码整齐,傍晚的时候装上一辆大三轮车上,然后父亲吃完晚饭就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出发了,几百斤上千斤蔬菜,一个人,一辆三轮车,人力蹬几十里到七宝的蔬菜批发市场,熬着夜把蔬菜卖给二道贩子,然后再蹬几十里三轮车回家补半天觉。我去过那样的地方,在一个夏天的夜晚,那是一个脏乱不堪,蚊虫肆虐,嘈杂无比的地方,但是我看到很多人把菜卖完后就直接在路边铺着一张草席睡了,因为他们太需要睡眠了,因为他们第二天还有活要干呢!慢慢地我从老爸回来的时间就可以判断出最近的蔬菜行情好不好,有时候天没亮就会到家,那个时候菜价高并且卖得快,这种情况下老爸带回来的空菜框子底经常会压点东西,比如说带给我和姐姐的饼干零食,给家里买点日用品,还有轮换着买一些鸡鸭鱼肉回来。如果太阳高过东边的房顶还没回来,那么那天的菜卖地就很便宜,或者没有卖掉倒在了垃圾堆里,一两天就白忙了。种蔬菜是非常辛苦和熬人的活计,我只是看在眼里,我就知道这个苦我一定吃不下,而父亲为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和作为儿子的责任,都一一吃下了……
爷爷的病在我9岁那年终究是无力回天了,我们接到电话从上海往家里赶的过程我已经忘了当时的场景了,我只记得农村的葬礼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喧闹和杂乱的,我很想有个安静的地方呆着。爷爷是我经历的第一个亲人离去,我没有掉眼泪,一来对于死亡的理解不够深;二来我觉得是坚强的孩子,我是不会哭的。以至于这么多年来,走了那么多人,我都没有哭过。作为长孙,我抱着爷爷的遗照,灵车出发时挂在路边树上的那一挂鞭炮就像放屁一样的上气不接下气。我愣了一下,就钻上了车。整个过程,我只看到父亲擤了几次鼻涕,眼睛红红的,兄弟几个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听从着几位老人发号施令,女儿和媳妇们则哭的昏天暗地。
从此以后,一大家子的主心骨就没有了,几个兄弟和姑姑都跟着我爸去了上海种菜,奶奶一下子成了留守的老人。奶奶年轻的时候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存在,当然也是爷爷给了她那样的幸福,当这些都一下子荡然无存了。
爷爷的离开,像丢入塘里的石头,激起涟漪,也终归于平静。老宅子还在的时候,爷爷的遗照一直摆放在我家土房子的案头东边,偶尔回去还能看到。后来房子没有人住,房子倒了下去,遗照也就收起来了。伴随着房子倒下,我们一家人也就没了归处,变成了彻底漂泊在外的一家子。
父亲继续熬着夜种菜卖菜,但上海的快速发展让种菜人想安稳的养肥一块地成为奢望,因为修路建房几乎每隔一两年,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一切从头开始。地是租上海人的,补贴赔偿天经地义的与我们无关,在通知的时间把东西搬走找另一个地方,才是最最重要的。那些地里的菜,会有当地的上海老奶奶们帮我们打扫干净,不会被浪费掉,当推土机开来了,辛辛苦苦翻种出来的沃土,就成了渣土车一趟趟拉走的废土方了。最不舍的就是第一个房子,再后来搬家已经习惯了,父亲估计也累了不想再多费心力去那么认真地盖房子养地了,索性有人不种菜了,他就把别人的房子和地接过来继续干,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地整得更规整,把菜种的更漂亮更好,卖的价格更高,挣更多的钱。至于房子,已经简化成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以至于那年高考结束,我去上海父母身边过暑假,看到了子女不在身边的房子,让我看了心碎的地方。
由于学籍的问题,我在上海念了5年的私立小学后不得不回安徽继续学业,寄宿在姥姥家去马头镇的中学继续读初中,从此以后我的书上再也没有父亲漂亮的签字,只有偶尔电话的叮嘱和卡里变多变少的余额。在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日子里,他们一定过的很辛苦吧!我时常在家会这么想,每当这么想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到睡着。
在我从初中到高中的六年,父母带着一家的叮叮当当,在上海搬了又搬,我每次暑假去他们身边的环境都是陌生的。可能他们自己也疲惫了吧!后面去了绍兴的壁纸厂里打工,投奔我三叔。去了温州的电镀厂里打工,投奔我小姨父。记得那年桑美台风的时候,我去了温州,他们住在昏暗潮湿的廉租房里,没有窗户,厨房就是一间屋子里面用压缩纸板隔了一块地方出来。我在家里看到老鼠在床上吃着蟑螂,我在家里呆着被房东闯进来把我刚换的节能灯泡拿走换上100瓦的白炽灯,我看到父亲的手臂胳膊被电镀的药水腐蚀的都是红色疹子,台风过来,我在家里呆着担心房顶被台风刮走……我讨厌温州那个城市,我想让他们离开那样的地方。
我的高中三年有幸在毛坦厂中学度过,那的确是一个好学校,我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校长坐在大门口,笑着和路过的学生打招呼,可以说那里的几乎所有的学生除了学习就没有别的事情做了。可惜当时身体底子不好,经常感冒咳嗽,在学校门口的私人诊所看病,怎么都看不好,挂了无数的水,吃了无数的药。幸运的是我毕业的第二年,那个私人诊所被抄了,原因是一个学生和我一样在那里看病一直看不好,他的爸爸是六安市卫生系统的官员,去看孩子的时候发现医院用的很多药品都是假药。
父亲在我一次连续病了很久都没有治好的情况下,从温州回来到学校来看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知道他会来但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学校。我记得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在教室外的阳台上透气,上课铃响起的时候我转身准备回教室,一转身看见走道上父亲笑着向我走来,我当时哇的一声就哭了,我看到他的脸色被电镀的蒸气熏的没有了血色,手和胳膊上都抓烂了,眉毛也掉光了……我摸着他的手拉着他往楼梯口走,迎面走来了这节课的政治老师,我哭的来不及和所有人请假,挽着他的胳膊往校外走,当时校长和保安队长坐在校门口,看见我也没有拦下我问我要请假条,出了校门往租的房子走,半路上还被衣服上趴着的蜜蜂叮了一下手指,所以就干脆一下子哭到了出租屋里。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心痛……后来听我妈说,下午我上课的时候父亲在我房间里看到我抽屉里,柜子里全是药的时候,也是在和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哭的很难过,说我在这里一定受了很多的苦。
那年冬天过年的时候电镀厂里放假,爸妈都回来了,因为老家的房子已经不在了,所以就在我外公家过的春节,我背负着不懂事的骂名,得罪了很多亲戚,以爸妈再去温州我就不继续念书为威胁,把一个人锁在屋子里,不见所有人,成功的让我爸妈又继续去了上海种菜,当时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吧!而我不知道那时应该把他们也逼的无路可走了吧!
13岁开始,这么多年与父母聚少离多,有时候会觉得有些陌生的感觉,即使现在偶尔在一起也不知道说一些什么。有时候在岳父家他们一家人吃过饭在一起聊很多事,我只是在旁边默默听着不说话,内心还是有些许羡慕,因为自从我记事起,家里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情景,都是在为了生计和我的学业奔波。现在虽然条件好了很多,但是那些本应属于我们一家人的时光,便再也找不回了。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评论列表
- 这篇文章还没有收到评论,赶紧来抢沙发吧~